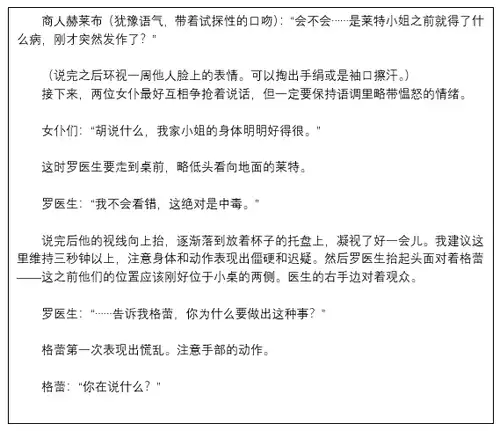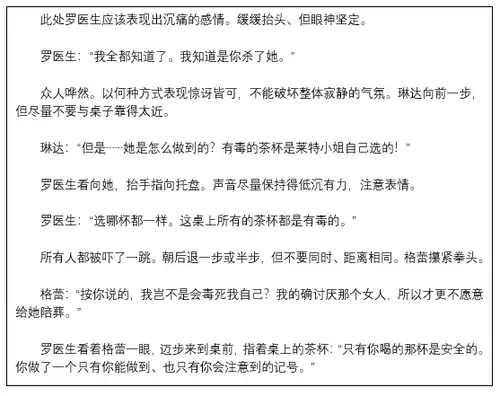古人常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樣的話,也有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樣的典故存世,大概的意思都是說人世間的好運厄運皆是頗為無常的事情。但我個人卻更信奉另一句話,也就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世上的好運往往難交,但厄運降臨到你頭上時可不會給你一點兒面子。
比如今天就是這樣。對要在清早辛苦爬起來去上學的學生來說,周一這個日子已經足夠晦氣了,更糟糕的地方在於昨晚我為了破紀錄上頭打遊戲打到半夜,醒來腦子昏昏沉沉的,一閉眼全是像素點。姑姑最近正頗為認真地執行着她那套以我看來不過三分鐘熱度的晨練計劃,樓下也果然沒有她的身影,但我猜測她的心情一定不怎麼樣。證據就是,她的廚藝一向還不錯,放在桌上的早餐卻實在是難以下咽。出門都快走到路口我才發現自己連衣服都沒換,只好又折回去。等到我緊趕慢趕地到了學校,已經是大門行將關閉、德育老師和學生會成員紛紛掏出小本本準備記賬的緊張時刻了。
儘管因為“君子協定”的原因,我不會因為遲到這種事而遭到懲罰,但在眾目睽睽之下進入教室畢竟也要承擔相當沉重的心理壓力,所以我走得明顯比平時要快。當然,校園內的變化大到哪怕是再行色匆匆的人也能注意到:原本只在圖書館的一隅暫為宣傳、被艾原嗤之以鼻的那名作家的肖像被印成大大的宣傳畫,貼在公告欄最顯眼也最亮堂的位置上;社團大樓上像拼畫一樣星羅棋布的招牌和橫幅多數也被撤下,換上了一條帶有他名字的、極盡諂媚之能事的歡迎語。事先說明,我對於這人並無情感上的好惡,以我那點兒可憐的文學水平也沒法對他的作品作出任何評價;但即便是這樣持着純粹路人態度的我,走在那條“恭迎著名作家來我校蒞臨指導”的條幅下也不由得感到脊背一陣惡寒。最讓人驚訝的是,那副已經完成的壁畫消失不見了,原來的位置上只留下了剛上好還沒幹透的紅色油漆,整面牆一片空白。我站在這既後現代又戲劇化的荒誕廢墟前愣了一會兒,隨後才反應過來——恐怕這上面的內容也必須要改成和那個作家有關的東西吧。
我無端聯想到那種用模具培養出來的方形西瓜。
沿着瀝青路向前,穿過花園,進入教學樓,我要去的教室在第四層從左開始數的第三間。這段我閉上眼睛都能走的路是如此程式化、如此具有目的性,以至於在路途中讓人覺得自己不是某種碳基的、有生命的活物,而更像是某個大型機器人的一部分,一個齒輪——尤其是在有無數和你穿着同樣衣服的個體在同樣的軌跡上行進的時候。
還是因為路修得太長了啊。這所學校有兩處大門,不論是從哪個門走到教學樓都需要五分鐘以上的步行時間。清晨漫長的上學路堪比睡前的淋浴間,都是最容易讓人變成哲學家的場景。毫無建設性的胡思亂想極其容易讓人覺得疲憊,等終於爬上四樓之後我感覺自己的意識都有些迷離了。還好今天的第一節課是數學,那位上了年紀的老師根本不在乎課上的學生睡成什麼樣子,坐在最後一排掌握了地理位置優勢的我那可真是得天獨厚……
然後我就看到教室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
在走廊上圍出這麼一團足以阻礙交通的人群很罕見,尤其現在還是早上。有不少像我一樣搞不清狀況的人停下來駐足觀看,隱約能聽到有女孩的哭泣聲。原本不願意湊這個熱鬧、準備徑直走進教室的我驚訝地發現引發事端的兩個人自己居然都認識。生平第一次,我不顧周圍人的冷眼極沒禮貌地用手臂破開一條縫隙,奮力擠進風暴的中心。
正和別人對峙的巫帆怔了一下,循聲望向我所在的位置。立在她對面的女孩哭的梨花帶雨,雙手不住地揉着眼睛——即便如此我也能認出那就是幾天前來圖書館借書的女孩子。從巫帆臉上看不出任何形式的情感波動,嘴唇緊緊地抿成一條線,只有耳根稍帶些紅色,像是剛和人吵了一架。
我自認對眼前這個從小相識、知根知底的女孩還算是比較了解,正因為如此才會比在場的所有人都更難接受眼前的現狀。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相信巫帆會與別人引發衝突,更不要說是比自己小一屆的學妹。
……我甚至都沒聽過她高聲說話。
印象與現實的差距帶來了極大的疏離感,伴隨着睡眠不足的睏倦一起衝上大腦,讓我有點兒恍惚。周圍的視線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身上,我能明顯感覺到血液正衝上臉頰。但眼下這情況已經管不了那麼多了。
“出了什麼事?”
巫帆的嘴唇動了一下,隨後便轉頭不再看我。她的視線放得很低,我一度以為她不會回答我的問題了。
“……只是我們社團內部的一些……事情。我們……我決定把那個劇本撤下來,不會在藝術節上參演了。”
女孩用最平靜的語氣說出了最令人難以置信的話。有一瞬間我都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了。
“……為什麼?”
“已經是決定好的事情了。”
巫帆說這話的時候直直地望着對面的女孩,話的內容也更像是衝著她而非衝著我。女孩睜着盈滿淚水的雙眼愣了一會兒,旋即便捂着嘴巴跑開了。人群自動為她讓出一條道路,我抬起手臂卻根本不知該如何挽留。巫帆仍舊挺着胸脯立在原地,手指絞在一起。我吐了口氣,轉身走到巫帆面前。
“我和你說過有事可以找我商量。”
巫帆移開視線:“我也沒遇到需要你幫忙的事情。”
“沒鬧這麼大的話我說不定就信了。”
女孩抬起頭看着我。她抱着胳膊朝後退了一步,身子都快貼到牆上了。
“那也只是我參與的社團內部發生的矛盾而已,說穿了就是我個人的私事。我沒有把事情告知你的必要,你大概也沒有在我面前咄咄逼人、追問個不休的立場吧。”
……也是啊。
我感到一陣近似悲哀的沮喪。不僅是源於自己的無能,更多的是因為自己居然逼着她說出了這種根本不像是她會說的話。
“你說的對,是我唐突了。對不起。”
巫帆的睫毛顫抖了一下,身體似乎縮得更小了,上身卻依然直直地挺着。四周的看客越圍越多,有些人甚至開始交頭接耳,事到如今我已完全不知該如何收場。
“嚯,這麼大一群人啊。是不是都嫌自己德育分太多了、急着想被記過是吧?”
班任不知何時出現在人群外圍,用老師對學生的那種特有的洪亮腔調吼出這句聽着像調侃實則明顯是威脅的話。原本堵得像圍牆一樣的眾人頃刻便作鳥獸散,有兩個莽撞的傢伙差點撲到了我的懷裡。
——救世主偶爾也會穿高跟鞋啊。
女人端着胳膊默默地看着眼前這些學生跑光,隨後又走到門口將教室里那幾個探頭出來看熱鬧的人像敲地鼠一樣趕了回去,這才來到我和巫帆面前。她先是打量了一下我倆臉上的表情,隨後便一如既往地擺出那副看着像是不懷好意的微笑。
“具體什麼事兒我也就不問了。是你們兩個人的話情況反而簡單了,什麼都懂,我也就不再多費口舌。就一個要求:盡量別給我添麻煩。今早這事兒好歹是給我先發現了,要是給那些專門抓小辮子的看到了,不得連着我一起到教導主任那兒參上一本?聽那老頭兒喋喋不休地訓個半天可沒勁透了,你們也得為我考慮考慮不是。”
巫帆機械的點着頭,我則一聲不吭。女人盯着她看了一會兒,忽然鬆了口氣。
“算啦,別在這兒杵着了,都回去吧。對了,巫帆啊,”女人突然停住腳,“徐老師讓你儘快去她那兒一趟。我先給你打好預防針,戲劇部的事情讓她這個指導老師非常生氣。”
女孩垂下頭:“嗯,我知道了。”
“那就好,反正我是把話帶到了。噢,還有,”女人偏過頭沖我擠擠眼睛,“別的事兒我也沒忘,等有時間會找你算總賬的。現在暫且先記着吧。”
我毫無反應地從她身邊經過,進入教室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不是因為我不相信她的威脅、事到如今還心存僥倖她會對自己網開一面。
——而是來自班主任的所謂懲罰,在現今的情況下真的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大概初中那會兒吧,我看過一部由知名推理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劇中的主人公是大學物理系的副教授,在已經掌握了所有事實、準備揭開案件真相之前的那一刻,他總是會掏出馬克筆、粉筆或者因地制宜地撿起樹枝和石子,俯身在目之所及離己最近的平面上默寫上一整面的物理公式。配上背景樂里極為帶感的電吉他旋律和演員本人俊朗的面容,整個場景儘管看着有點兒荒誕,但更多還是帶給觀眾一種高深莫測的瀟洒感。根據劇中角色的自述,這樣做有助於他釐清思路、更快得出正確的結論。
我是文科生,自然也就無法測試這一方法的可靠性,畢竟過去學的那點兒物理基本已經原封不動地還給老師了。但我能為之作證的是,數學公式對於理清邏輯是一點兒幫助都沒有。這裡必須要感謝一下我們五十多歲的數學老師不辭辛勞地寫了那麼久的板書,但我盯着那一黑板的導數公式看了四十多分鐘,腦子裡仍舊是一團亂麻毫無頭緒。可能是因為課上教的這些還不夠深入吧——和艾原平日里給我單方面灌輸的那些不定積分線性變換之類的、天書一樣的東西相比,黑板上的這些式子起碼還屬於正常人能看得懂的範疇。
……只不過對我的思考毫無幫助。
下課鈴響了。還在黑板上奮筆疾書的老師愣了一下,慢慢轉過身望着我們,似乎沒想到往常和一整個世紀差不多難熬的數學課今天居然會結束得這麼早。他推了下眼鏡,用極低的聲音說了聲“下課”,隨後便夾着教案離開了——就好像是在害怕把伏桌沉睡的那些學生給吵醒了一樣。清晨的瞌睡蟲似乎更難戰勝,絕大部分人還都趴在課桌上。我也俯下身把頭貼近臂彎里,但拜早上的插曲所賜,困意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喂。”
有人敲了下我的胳膊。因為是熟悉的聲音,我並沒有理會。
“喂!別裝死了,快起來。知道你沒睡。”
我懶洋洋地調整了一下姿勢:“明明知道別人有正經的名字,卻只用語氣嘆詞來稱呼,這不管放到哪兒都是極為不禮貌的行為吧。”
下一秒鐘,我就被人揪着衣領拽了起來,視線對上了一張氣鼓鼓的臉。宮羽華左手叉腰,右手提着我的后脖頸,一副有什麼東西鬱結於心卻又不得不發的樣子——像是在超市大酬賓開始前被攔在門口的主婦,或者是剛踏入自助餐店、正準備要吃下一整頭牛的食客那樣。
“跟我來。”
她只簡單地說了三個字。
在一所公立普通高中里四處探險並非多麼吸引人的事情,尤其是在僅僅十分鐘的課間休息時間裡。好在宮羽華要帶我去的也不是什麼偏遠的秘密教室之類的地方,而只是樓下的自動販賣機。她從機器里按了兩瓶罐裝咖啡下來,我想掏錢卻被擺手制止了。
“算姐請你的。”
樂得從命的我坐到路對面的長椅上,霍地一聲拉開拉環。宮羽華挨着我坐下,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裡的飲料罐。
“巫帆那件事,你想明白了嗎?”
女孩開門見山。我啜飲了一口罐里的咖啡。味道還湊合,只是對於正經的咖啡來說這口味還是太甜了。
“你不是也聽到她是怎麼說的了嘛。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我哪兒來的資格去指手畫腳。”
身邊的女生一下子站了起來:“我說你是不是傻了,連違心的話都聽不出來?因為別人一時上頭說的氣話就耍脾氣鬧彆扭,我真沒想到你是這麼一個小肚雞腸的人。”
我看着她氣鼓鼓的臉頰,疲倦地吐了口氣。
“我當然知道她心裡不是她嘴上說的那個意思。巫帆不是會被情緒推着走的人,不可能憑着一時衝動就說出會讓自己後悔的話。她不惜冒着刺傷我的風險也要把話說出口,一定有她的目的。“
“那——“
我用眼神示意她坐下來。宮羽華目不轉睛地望着我,我仰脖將罐子里的飲料喝乾。
“怎麼解釋呢……今早的巫帆給我一種感覺:她不是不情願讓我幫忙,反而更像是害怕我真的會解決她面臨的問題,才會從一開始就質疑我插手的立場。所以你問我會不會因為巫帆說的話而不高興,那沒有;但是不是因為沒法對現狀做出任何改變而感到沮喪,肯定。”
我抬手把飲料罐扔進不遠處的敞口垃圾桶。宮羽化的視線跟隨着那東西在空中劃過的弧線,而後“呼”地嘆了一聲。
“你還記得那天嗎。下雨,我們幾個都在圖書館。”
“嗯。”我回到椅子上。
“那之後我就跟着巫帆去社團開了會,討論藝術節上要演的劇本。之前大家一致同意要排那個《雷雨》,不少人原著都讀過好幾遍了,演起來得心應手。但郁蘭——也就是你早上看見的那個妹妹、我們社團里負責寫劇本的——一直堅持說要寫一個原創的推理故事。大家拗不過她,最後也就同意了。”
我望向前方:“聽起來其他人好像都不太信任她。”
“……多少有點兒吧。其一是,我們之前演過的兩個本子都改編自名著,還沒嘗試過原創;其二是,至少我覺得,她……”
“她並不是特別了解推理。”
“……嗯。雖然我也不太懂什麼推理啊懸疑之類的,但我知道這些都是很複雜、很費腦子的東西,得那些特聰明的人才能搞明白。郁蘭是個勤奮的好孩子,可她平時看着根本不像是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樣子。我們都覺得她是被那個講座上的作家給洗腦了,才會這麼執着於推出和推理有關的劇本。”
怪不得當時會一次性借走那麼多推理小說啊……現在看來應該是當成考前惡補的資料了。先不論這一做法的效果如何,那女孩肯定也是拿出了認真的態度去對待,要說是一時興起也未免有失偏頗了。
我站起來活動了一下肩膀。從出廠以來十幾年間從未上過潤滑油的脖頸發出令人不悅的喀啪聲。
“然後呢。特意把我叫出來,接着還告訴我這些,你心裡一定有自己的猜想了吧。”
宮羽華瞪着我,隨後翻了下白眼。
“你知道嗎,有時候你這種就很讓人討厭。”
我不知道她所說的“這種”指的是什麼,只能無辜地聳聳肩。好在她看起來只是不想放過任何一個數落我的機會罷了,很快便回歸了正題。
“事先說好,我不覺得我想的就百分之百是對的,只是早上一看到她們吵起來就回想起了之前發生的事情。她們兩個估計是因為劇本的長度起了衝突。”
說到這兒宮羽華抬起頭,像是在揣摩我臉上的表情變化。
“周六的排練你不是也來了嗎,劇本在前一天的下午才完成。我也說了,我對推理這些一竅不通,沒法評判故事寫的好還是不好,在我看來至少還挺熱鬧的。但劇本整體上有一個沒法忽略的問題,那就是太長了。”
“是因為時間有限台詞記不過來還是……”
“也有那方面的原因吧。”宮羽華笑笑,“畢竟不到五天的練習時間真的不夠用。但更主要的麻煩出在演出時長上。按藝術節的規定,單項節目的演出時間上限也就是三十分鐘,而按照原本的劇本設定排完絕對會超過一小時。”
啊……
“於是在那天的討論會上,經過大家的一致同意,劇本被砍掉了百分之四十的長度,我們試演時候排的也就是精簡后的劇本。但就是現在的這個本子,演完前四幕時間也超過了半小時,根本沒有給結局留出時間,勢必還要再次刪改。那就……”
宮羽華欲言又止。
拿出任一領域作為參考系,我都算不上有半點才能,更遑論成為某種形式的創作者了,難以設身處地地代入女孩的心境。但只是泛泛地設想下自己投入心血和努力的成果竟然要因為這種理由就要被刪減的面目全非,大概誰心裡都不會好受吧。
“那劇本目前的情節已經很跳躍了。”
“還不止這樣呢。”宮羽華的聲調頗為低沉,“還得把立定跳改成三級跳才能符合要求。我也不理解巫帆為什麼這麼匆忙地下了決定——按道理這麼大的事起碼該和大家商量一下的。昨天下午她突然在群里發了一條消息說要棄演,之後就再沒信兒了。現在部里的其他人應該比我還懵吧。”
我對相關的規定一無所知,但退演應該不是比如舉手站起來說句‘我要取消演出!’就能輕鬆地全身而退這麼簡單的吧。我將想法告訴宮羽華之後,女孩不由得露出苦笑。
“想的倒美。先不說學校層面的問責,所屬社團的指導老師第一個就不答應。不過看巫帆那樣兒,估計她想自己一個人全部扛下來。”
“那她會怎麼樣。”
“能怎麼樣。”宮羽華攤開手,修長的手指像有彈性的枝條一樣上下晃了晃,“大不了就是被老師從社團除名唄,反正到下半年也要自動隱退了。她肯定早就做好了要離開的心理準備,只是不能接受這種離開的方式吧——讓一個沒完成的企劃成為自己在社團里做的最後一件事。”
可能因為起風了,她忽然扣上了兜帽,抱着雙腿縮成一團。
“……我也不能接受。”
我看着那微微顫動的帽頂,輕輕咬了咬嘴唇。
“所以你覺得巫帆和那女孩是出於被迫要對劇本進行刪改的原因就起了爭執?”
尖尖的兜帽頂朝下一沉。我嘆了口氣。
“決定是大家一起做的吧,多少也有點迫不得已的意思。我不覺得那女孩是不明事理的人,說她因為這點就把罪責一股腦記在巫帆頭上,這未免也太牽強了。”
“所以我才說那只是‘我個人的猜測’而已啊。”宮羽華一下子掀起腦袋,“反正我知道的已經全都告訴你了,要怎麼做就看你自己了。”
“……恐怕巫帆並不希望我真的做什麼。”
“管她怎麼想的幹嘛,想想自己要怎麼做才是關鍵。一個大男人做事怎麼這麼瞻前顧後的。”
女孩說著,起身拍拍褲子上的灰塵,將手裡那罐沒開封的咖啡塞進我的口袋。在她蹦跳着跑上門前的台階之前,我開口提了個小要求。
“給我看看你手裡的劇本。”
對事物所懷着的執念幾乎是最累人的情緒了,哪怕是在旁觀者看來。
你可能對什麼東西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地付出一切,但最後做出評判、把握生殺大權的人可能一點兒也不關心——甚至根本不曉得這東西是什麼。比起在乎自己“要以何種方式離開”這種事情,從一開始必須要離開的這個決定就有很大問題。
……不過說到底我也不是當事人啊。
我拉開椅子坐到櫃檯後面,從包里掏出宮羽華借給我的劇本。她把這東西丟進我書包之後沒說上幾句就匆忙跑去訓練了。這幾天她一直跟在戲劇部這邊,其實下個月就要參加全市高中聯賽的籃球隊催得更緊。和她差不多時間離開的還有巫帆——這是我近兩年以來第一次看到她早退。下課鈴響過之後她和老師打了個招呼,隨後便背起書包無聲無息地從後門走掉了。我看着斜前方空蕩蕩的座位,忽然感覺靜不下心。
於是我也溜出來了。
多數人還在上最後那兩節課,閱覽室里空無一人。我拉上身後的窗帘,開始閱讀這本我已經看過的話劇。
首先讓我覺得驚訝的就是劇本的細緻程度。從字體能看出這是手寫稿的影印版,上面密密麻麻地畫著刪除符號和劃掉用的橫線。依照這份原版的劇本,整部劇足足有七幕,前面用了很長的篇幅來介紹出場人物的恩怨,只停留在背景介紹或者是人物敘述里的事件按原案其實應該是發生在舞台上的。後面的劇情主幹也有不少的刪改,比如原文里的那三組人都是處在各自獨立的場景,而出演時則大概是出於現實道具方面可行性的考慮,把他們整合在了一個大場景里。最明顯的是在對演出細節的描繪上,幾乎每句台詞之間都夾雜着大段的心理介紹和動作描寫,巨細靡遺到不僅介紹了演員的站位和動作,甚至不厭其煩地囑咐了當時該採取的視線方向和表情。演員們普遍僵硬如木偶般的表演實在是怨不到他們,因為劇本真的沒給他們留下太多的發揮空間。
我沒寫過任何形式的東西,自然對創作的具體過程不甚了解,但即便是以旁觀者的角度看這種程度的寫作也是相當耗費腦細胞的。之前對劇本作者是否遵循了邏輯性的擔憂完全是在杞人憂天,劇中所描寫每一個場景顯然都經過了仔細地推敲。其實在翻開劇本之前,我就知道毛病一定出在故事的結局上。前面的部分已然經過了試演的測試,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應該當下就發現了。雖然整體的效果不算理想,但看上去還不至於存在讓劇本直接腰斬的大漏洞。基於此,我對那沒有上映的第五幕更感興趣了。
劇本並沒有多厚,從前面翻也很容易就能找到開始的那頁。這一幕的情節緊接上一幕的末尾,眾人在短暫的猶豫之後立刻將懷疑目標鎖定在格蕾身上,異口同聲地指責她是事先在飲料里投了毒。但格蕾抵死咬住一點不放:自己自始至終沒有碰觸過被害人手裡的茶杯,而那隻杯子是被害人自己選的。如果是無差別地在所有茶杯里都投了毒,那就沒法解釋同樣喝了茶的她卻毫髮無傷這件事。無法解釋這點的眾人又將目光轉到另外兩個嫌疑人身上,但最終兩人以一種在我看來很沒有意思、卻也理所應當的方式排除了嫌疑——他們的身上並沒有攜帶毒藥。案件一時陷入僵局,眾人都沉默不語。 接下來的部分,我覺得直接援引原文可能更方便些。
——所以果然是杯子的問題。我回想起在巫帆拆箱時看到的那個單獨包裝的茶杯。但……我不知道。
這是個頗為古典的故事,大家從一開始就知道是誰犯了案——或者說誰最有嫌疑,只是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也因此,劇中並未出現專職的偵探角色,結論是由唯一的專業技術人員羅醫生得出的。純粹從詭計設計的角度看,對一個從來沒有接觸過推理作品的新手而言這樣的想法堪稱精妙。
唯一的不妥之處在於,這和我曾經看過的一本小說里出現的橋段幾乎一模一樣。
我盯着桌上的劇本看了一會兒,朝前拖拖椅子,打開桌上的電腦。老掉牙的機器發出刺耳的轟鳴聲,硬盤唧唧直叫。
我想找來作對比的那本書早在半個月之前就被借走了,而且到現在還沒還回來。
來回確認過十幾次之後,我丟開鼠標,重新將視線轉回到面前的劇本上,百無聊賴地翻動着。
劇本的扉頁上寫着“暫定”標題以及演出人員表,角色大概是按照出場戲份的多寡排列的吧,格蕾的名字排在最上面。演員名與角色名一一對應,只有格蕾和萊特後面的出演人員名字遭到過塗改,留下兩塊頗為糾結的黑斑。話說,那些女僕居然也有正式的名字啊,比如其中一個女僕就叫珂賽特,看起來比主角的名字都用心多了,只是劇里從來就沒出現過。可能那個叫郁蘭的女孩兒和我一樣不擅長起名字……
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之後,我將劇本遠遠地推到一邊。這種沒法確認疑點的溫吞感真讓人不舒服。雖然憑記憶推斷也算大差不差,但那畢竟不是靠譜的實證。
——記得西門外面好像有家舊書店。
我訝異於自己在這件事上的行動力。幾乎是在冒出這個念頭的同時,我起身把劇本塞進包里,鎖上閱覽室的門,下樓朝校門口走去。